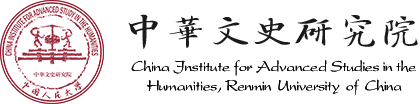论坛纪要 | 西方经纬知识与清代方志的星野书写
发布时间: 2021.1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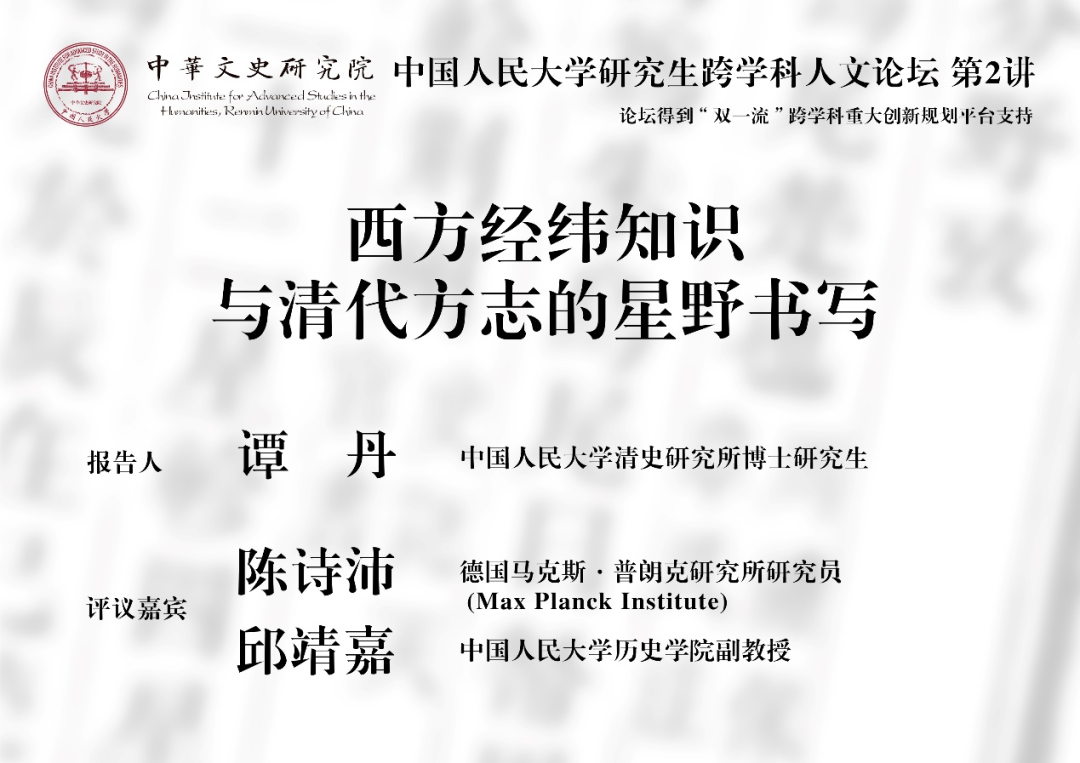
2021年11月1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跨学科人文论坛第2讲在清史文献馆举行。本次论坛报告人是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谭丹,报告题目为“西方经纬知识与清代方志的星野书写”,评议环节邀请到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陈诗沛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邱靖嘉副教授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雷天月主持本次论坛。
报告内容
中国古代的天文分野之学以天星对应地域,承担着古代天人感应的寄托。明清方志卷首多为“星野”“分野”“星土”等篇目,来概括当地所处方位。而西方经纬知识的传入带来了新的坐标体系,使分野学说开始不断调整其繁杂的体系,以适应和容纳新的认知和学说。
谭丹的报告便以方志为切入点。她发现在西方近代天文知识传入之后,地方志编纂者开始权衡星野和经纬知识。在时间上,乾隆钦定的《热河志》开启了删星野、立“晷度”的先例,说明了统治者对经纬之见的认可。但这一时期经纬知识在方志中仅是零星出现,直到同光时期才出现大量新列晷度的方志。反观,中国传统的星野学说并未受到冲击而消退。事实上直到民国还有许多地方志依然采用星野学说。在空间上,对经纬晷度的记录呈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例如湖南、广东、直隶等地的方志走在了吸纳经纬知识的前列。谭丹认为这与地方开放程度、编纂群体新学新知的吸纳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
方志编纂对星野的处理方式也是多样的。多数方志虽保留了星野一卷,但由于在星野学说方面“歧论纷纷”“聚讼不休”,许多方志或是先列星野而加以批评,或是把星野学说的是非论断悬置起来,仅注“以备参考”;而吸纳经纬知识的方志,则多以晷度并入星野一卷。此外,方志中虽有记载晷度,但所记经纬度数据很少实测,多来源于一统志、《经纬度表》等资源。直到光宣时期,经纬度的实地测绘才普遍开来。但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星野体系一直在尝试将西方经纬知识纳入其中,并进行糅合。


陈诗沛研究员结合自身在马普所进行的LoGaRT地方志研究群的经验,肯定了“晷度”在方志当中的特殊性。她指出方志从记载传统北极出地度,到晷度,再到经纬度,有一个三层转换的过程,学者需要考察晷度如何进入方志,并逐渐完成从星野到经纬的过渡。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追问,在地方没有实测技术的情况下,方志引入的经纬数据背后是否存在着知识的流传网络和系统?此外,陈诗沛老师还提到,在乾隆对星野进行了彻底否定之后,地方志还长时期延续着星野的书写。研究者应该如何解释这种顽固的守旧性?这是否代表清代官方对地方志内容没有过多话语权?她认为在清代之后的方志编纂中,中央似乎没有过多限制,所以乾隆公开对星野学说表露疑问之后,许多地方志编纂者仍没有摒弃星野学说。而且星野书写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背后也暗含了地方志编纂者群体在文化上的守旧性和社会上的滞后性。

邱靖嘉老师首先回顾了历代方志中出现星野、分野、分土的历史背景。根据他在《天地之间》一书中的研究,大致宋代以后,各类地方志开始出现了对分野情况的普遍记述。明末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就已经影响了地方志的编纂,方志中也出现了晷度。至清代乾隆明确否定天文分野学说,以及钦定《热河志》删星野、立晷度之后,许多方志也沿袭此种做法。但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星野被淘汰的过程相当漫长。正是因为宋以来地方志都记载分野,到了晚清以后,虽然人们早就认识到这一套知识的荒谬,但仍然保留在序言、按语中。但这时保留星野的方志,大多数只是作为传统知识的面貌呈现,他在书中将之概括为“文化史知识的保留”“历史知识的遗存”。然而,从地方志编纂者的按语中,可以看到编纂者大多数对星野还是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只是囿于传统方志的固有体例加以留存。因此对数量大、同质化程度高的地方志资料,除了要使用量化进行整体分析之外,还需要对典型个案进行单独分析。另外,方志当中有丰富的图像资料,如经纬图、分野图、星象图等,图像也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西南、西北、东北、内蒙等边疆地区的方志,不仅仅有经纬取代星野的现象,还暗含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对此,陈诗沛老师也补充到,边疆地区的方志到了晚清反而加入了星野信息,这是因为边疆地区此前在中原星野版图之外,到了晚清,地方需要借用星野一门来重新确认自身身份,因此星野也含有国家认同和地域认同的意义。这或许可以回答为何乾隆之后的方志仍然保留、甚至强调星野。
在交流环节,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张佳静老师也线上参与了讨论。她指出方志所记载的经纬度数据中,经度是更加值得关注的对象。晷度、北极高度都是纬度,在测量不够精确的情况下,这几个数值相近,因此对于受到“西学东源”的人来说没有差别。反之,研究者可以从经度数据的精细化过程进行分析,从而对比出知识的更新。另外,“西学东源”说对清代方志采用晷度、经纬度来记录方位产生了影响。例如,广东的地方志多采经纬度,而《广东通志》的主修者阮元就是西学东源说的支持者。张老师在用LoGaRT作方志中的经纬图研究时发现,清代大部分带经纬图的方志都在广东,而经纬度地图有时是将传统“计里画方”的图安上经纬的名,并非真实的经纬度,直到宣统朝才开始实测,这也揭示了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面向。此外,中国传统的晷度测量其实相当精确,传统的晷度到底有哪些缺陷,使得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不再采用晷度,而是代之以经纬度,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次报告展示了传统天文分野学说在近代的转变,讨论了西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等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下午四点,报告在意犹未尽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纪要撰写:谭丹 李翔宇
海报设计:褚可桦
照片拍摄:孙祎达
执行主编:雷天月